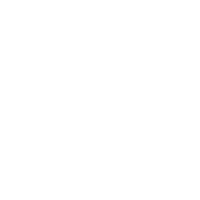杏雨流年
又是一个清晨,细雨洗过的天空格外亮丽。此刻,我已在小区旁山坡的杏林里了。当长焦镜头推近枝头的刹那,花瓣边缘的露珠在逆光里泛起珍珠般的光晕,这瞬间的映像,像极了儿时隔壁小囡的万花筒里流转的景致。那时她总爱在杏花初绽的清晨,摘一片花瓣放进万花筒,对着眼睛转啊转,活脱脱像一只快乐的蝴蝶。可如今,我换过无数次镜头,而在取景框里,却再也寻不到记忆里那个“杏花仙子”的模样了。

村子里第一朵杏花,总在清明之后踮起脚尖,叩响春天的大门。天空,一片让人心疼的高原蓝,晨露未晞,西头坡地那棵斜挂在石墙上的老杏树,早已洇开几点胭脂红。单瓣的花骨朵顶着绛色花萼,多像刚施过胭脂的小姑娘,眉目间还粘着未干的朱砂;复瓣的裹着层层绢纱,在晨雾里舒展,粉白的云翳从枝头漫向沟谷,不过三五日,整个山坳便浸在花的潮汐里了。此时,父辈的犁杖已碾过残雪尚存的田埂,却见两三片粉瓣落在犁沟里,恰似春天烙下的印章。

杏花的美带着骨子里的倔劲儿。那年倒春寒,鸡毛雪片裹着北风抽得枝桠“噼啪”作响,单瓣花却偏要在寒风中舒展——薄如蝉翼的花瓣边缘冻得微卷,仍朝着天空的方向翘起;复瓣花像永不服输的村姑,层层花瓣冻得泛青,却将最中心的花蕊护得暖融融的,恰似一只只精灵举着小灯笼,在树影里空行。春寒料峭中,杏花的倔强与农人抗争的身影相映。性急的新媳妇蹲在菜畦里伺弄冒尖的“洋韭葱”,指尖的葱秧旁,几片花瓣半埋湿土,蜷曲的细纹里透着不达春深不低头的韧。这哪里是花,分明是打开春天的钥匙,将农人的裤脚、犁杖的木纹、背篓的缝隙染上粉白,催着冻土下的种子出苗、拔节、开花、结果。

已往每年春天都会拍一些杏花,但总觉得所拍作品显得单调虚浮,很难达到畅快淋漓的效果。而在今早,当我把镜头再次对准这棵他乡田边的杏子树时,才终于明白我是要借着拍杏花之机,让自己的心回一趟家的呀。这时的杏花当用长焦拉近时,花瓣与云絮在取景框里摇曳,像儿时踮脚够花,鼻尖蹭到带露的温柔,连呼吸都会减慢下来;微距对准花蕊时,金黄的花粉簌簌落在镜头上,恍若老娘鬓角的白发在花影里闪烁。而花心那点胭脂色,原是少年记忆中的悸动,随着镜头轻微的震颤微微发烫;定焦屏气的刹那,眼前骤然闪现当年扶犁的那个人,为何总盯着地头的杏花——有些美好需要用整个童年的凝视来对焦,就像此刻微距镜头里的花瓣,每道纹路都刻着回乡的路径。人们说,“所谓乡愁,就是一场穿越时空的流浪,只为寻找记忆中的故乡。”而所谓摄影,不正是一场寻找故乡的流浪吗?

杏花花语在唇齿间流转时,忽然想起村里老人的话:“杏花是给土地报信的,花开了,地就该醒了。”那些在春寒里绽放的花朵,花瓣留着冰茬划过的细痕,花蕊藏着冻土的气息,却偏要在粗粝的山石旁、皲裂的犁杖边肆意开放。而当花瓣飘落,在泥土里渐渐没了踪迹,枝头就冒出了毛茸茸的小青杏,一个个圆滚滚的,像小拳头似的。看到它们,我又想起小时候,攥着花瓣在田埂上奔跑,跑完摊开手心,留下的那一道淡淡的粉色印痕 。

轻风掠过杏林,落英如细雨缤纷。镜头上忽然飘落一片花瓣,边缘还洇着晨露的淡粉——多像那年我夹在书页的那朵啊!原来最美的杏花,从来不是取景框里的定格,而是藏在时光褶皱里的某个清晨,是开蒙老师鬓边的银发,是山洼里的泉眼喷涌的水花,还有那个扎着花瓣奔跑的小囡囡,衣摆里兜着整个春天的芬芳。

文字:刘鹏;
摄影:刘鹏;
编辑:李雪薇;
主编:辛元戎;
总监:王丽一;